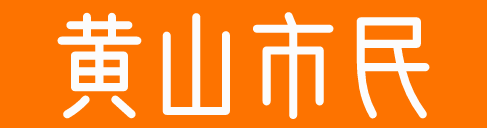每天读点故事app作者:绿风蓝海 | 禁止转载
旱烟的味道伴着一阵阵脚臭从下铺传来,孩子妇女男人的吵闹声一浪盖过一浪,我从梦中惊醒,外面的天已经亮了。
信纸被我紧紧地攥了一夜,手指有些酸痛,泛黄的纸张粗糙不堪,上面两行清秀的小楷被我的泪水模糊。是的,我捂着信纸哭了一夜。
我的父亲去世了。
十年前,我走出了那群大山,十年间我再也没有回去过,那是我的童年,也是我的伤疤,丑陋不堪的伤疤。今天是我第一次踏上回家的路,却是因为父亲去世了。
我不孝,父亲将我辛辛苦苦拉扯大,守着三亩旱地几头猪,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供出了山里唯一一个大学生,唯一一个博士,却没想到是个白眼狼。
近些年,父亲让兰姨给我写了好多信,信里说他想来我工作的城市,想看看我,跟我一起生活,想见见我媳妇。
我不是不知道父亲的想法,可是我哪能回应他?北京房价这么高,我跟媳妇还挤在六十平米的小房子里,哪还有他的地儿?况且,媳妇根本不知道我有他这个爹。
火车外的风景一闪而过,我有些头晕,就像小时候父亲抱着我轮圈子一样,周围的山啊、树啊、花啊、草啊一闪而过,还有那畏缩在猪棚里的女人……那个女人总是窝在一角,乱糟糟的头发下一双眼睛乌黑透亮,她的手脚上戴着铁链,链子随着她的动作发出闷哼的响声。她不会说话,但字写得非常漂亮,导师说这字体是小楷。
斜阳西下,火红的余辉洒在厚厚的雪地上,我拎着沉重的包裹,踩得积雪咯吱咯吱地响。包里是上好的白酒,父亲爱喝也爱炫耀,所以我每隔几个月都会往山里寄东西,啤酒、花生米、药,还有几百块钱。我想,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往回带东西了。
从火车站转客车再转拖拉机,等看到村里的第一盏灯火时,月亮已经高悬在枝头,我环顾四周,紧了紧衣领,迎着寒风往前走去。
十多年了,这里一点变化都没有,几十间茅草房从南往北坐落在山脚,北风呼啸,吹得它们瑟瑟发抖。山路依旧陡峭,我小心翼翼地往前挪动。八年前,四叔在这条路上摔了下去,摔得粉身碎骨,面目全非,有人说他是失足坠崖,也有人说是四婶的报复。
四叔死后,兰姨曾来信跟我说过这事儿,因为父亲跟叔叔们都觉得这是鬼魂的报复,一时之间人心惶惶,所以兰姨想让我回来看看他们。
但我当时正准备跟女朋友去丽江旅游,爱情面前亲情是不值一提的,尤其,她还是我导师的侄女,我必须为自己找个依靠。所以我只是写了封信回去,告诉他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无神论,我知道父亲他们听不懂,但我相信兰姨懂,因为马克思主义还是兰姨教给我的,虽然她不会说话。
说起四叔的死,我也怀疑是四婶的鬼魂回来报复了,这条路四叔走了三十八年,刮风下雨时都安然无事,偏偏在一个风和月明的夜晚坠了下去,而那天,正好是四婶的祭日。
寒风呜咽,刮得枯枝咔嚓作响,我的脚步声一下一下地响在山野,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清晰,我有些害怕,不该去想四叔的死,因为想到四叔就想到了四婶。
自从我记事以来,四婶就住在我家的地窖中,赤裸的身上青一片紫一片,手脚以诡异的姿势向下翻折。奶奶常常拿着根驴鞭下去给她送饭,父亲、二叔、三叔、四叔也常常下去看她。我有时会偷偷下去找她,给她送吃的陪她说话,但她眼神中常常是恐惧,是绝望,那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,那眼神跟兰姨的不一样。
我是第一个发现她尸体的,清晨的阳光从窖口射了进来,照在那摊红得刺眼的血液上,睁圆的双眼被头上流下的鲜血染红,正死死地盯着我,盯得我浑身发毛。
直到现在,我还能清晰地感受到当时的恐惧。不过我到现在都没想通,手脚残废的她是怎么一头撞死在墙上的。她的尸体被父亲跟叔叔们草草地埋在山沟沟里,赤裸裸地扔在了山间,但尸身下的血色符号却永远留在那里,即便擦干净了,第二天也会出现。
血色符号上面是两个口,下面是一条弯曲的小河,血液渗在地里,永远也除不去。直到现在我才知道,那根本不是什么符号,那是一个字,一个“咒”字,这是我第一个会写的字。
寒风呼啸,山间的脚步声有些凌乱,我定定地停下脚步伫立在那里,耳边咯吱咯吱的声音越发清晰,后背一阵凉气袭来,是四婶的鬼魂吗?
“方子。”
面前的黑影一瘸一拐,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,“是方子吗?”
“兰姨?”我有些惊讶,兰姨竟然会说话了,她的手脚上也没了铁链。
“快给我看看,看看我们家的大学生。”兰姨用她冰冷的手捧着我的脸,左看了右看,细细端详,“你可算是回来了。”
“兰姨,对不起。”望着她鬓角的白发,眼角的皱纹,还有瘸了的腿,我有些愧疚。
“对不起啥……唉,就是你爹,死前还念叨着你。”
我紧紧地抓着手中的包裹,声音有些颤抖,“我爹是怎么死的?”
“喝了点酒,就喘不上气了,活活给憋死的。”兰姨声音平平,完全没有痛苦或者惊慌的感觉。
“是我……是我的错,我不该给他寄酒。”
寒冬的天,电闪雷鸣,我有些害怕,怕遭天谴。
惨白的光照在兰姨的脸上,她回过头来似笑非笑地望着我,血红色的花袄在黑夜中有些瘆人,“你孝顺才给他寄酒,你没错。大家都说是你四婶子的鬼魂作祟,因为他的尸体下也出现了‘咒’字。”
我若有所思地望了兰姨一眼,没有说话。
家,还是记忆中的样子,矮小破旧的茅草屋,肮脏的猪圈,巨大的石磨,高大的槐树,一切都没变,唯一改变的,是他们都老了。
奶奶的背弯得像初一的月亮,颤巍巍的双手轻轻地抓着我。我抱着她瘦小的身体有些感伤,心里却想,不知她现在还抡不抡得动驴鞭。
二叔三叔也有些憔悴,站在奶奶身后拘谨地看着我,看来是被鬼魂弄怕了。
我急忙将手上的包裹打开,把里面的白酒与吃食拿了出来,“二叔,三叔,我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,就带了些平常的吃食,吃完我就去给父亲守灵。”
饭桌上,二叔三叔渐渐跟我熟络起来,酒一杯接着一杯,话也多了。
“方子,北京大不大,有看到国家主席吗?”二叔喝了几盅酒,有些微醉。
“北京大,不过也就跟我们大山一样大。主席忙着国家大事,我这样的小人物是见不到他的。”
“北京的女人好看吗?有你兰姨好看不?”二叔瞄了眼兰姨,吸了吸鼻子。
“你俩说,我去尿个尿。”三叔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,步子有些不稳。
我朝三叔点了点头,转而对二叔回道:“二叔,你是不是醉了?”
“嘿嘿,我没醉。”二叔笑眯眯地靠在我耳边,悄悄地说,“你兰姨真是个妙人,那床上功夫,啧啧,回味无穷啊。”
“二叔!”
我有些愠怒,兰姨是我最尊重的人,别人家的孩子光着屁股在山间撒欢时,我早就跟着兰姨学会了《三字经》,学会了唐诗,别人家的孩子捡粪球砍枝子的时候,我知道三角函数,会写英语。我这个大学生,可以说是兰姨一手培养出来的。
我尊重兰姨,不允许别人侮辱她,更何况,她是我父亲的女人!
“二叔,您是长辈,希望您说话有个分寸。”
二叔嘿嘿笑了两声,扯着我的衣袖让我坐下,“你就不想知道你娘是谁?”
是的,我活了三十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娘是谁。村头的二狗子说兰姨是我娘,但我父亲说我娘已经去世了。我想也是,我娘怎么可能生活在猪圈里?
“谁?”
“是你……”二叔还没说出是谁,便听到院子里传来一声尖叫,听声音是奶奶的。
我跟二叔噌地窜了出去,眼前的一幕彻底把我们的酒劲给吓醒了,是的,吓醒了。
奶奶晕倒在雪里,而她面前,是被吊在槐树上的三叔,他的身体赤裸裸地暴露在月光下,惨白的月色铺在被血染红的白骨上,血液顺着骨头的线条流了下来,滴在雪地上那一堆红白相间的人肉上,滴答滴答一下又一下。
三叔被活刮了,看他狰狞的面目就知道他死前经受过偌大的痛楚。
震惊与恐惧涌上喉间,胃里翻江倒海,我趴在地上吐了起来,二叔与兰姨也一样,受不了这血腥残暴的场景也趴在地上吐了起来。
“哈哈哈……”诡异的笑声从身后传来,我扭头望去,一个女人站在那里发疯似的狂笑,“死得好,死得好,你们都得死,都得死……”
“田儿,别发疯,快回去。”兰姨从地上爬了起来,勉强拽着那个女人往屋里走去。
我是真的害怕了,这里发生的一切太恐怖,我想回北京,想回到我正常的轨道上,这里太肮脏太黑暗太恐怖,我怕我走不了了。
“她是谁?”
“你三婶,脑子有问题,买来的时候就这样了。”二叔缓过神来,从地上爬起来将奶奶抱回屋里,又出来将我扶起,镇定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,“一块把你三叔的尸体放下来。”
三叔的血还是热乎的,粘乎乎地粘在手上非常不舒服,这不是我第一次触碰尸体,但我的手还是颤抖。
是谁杀了三叔?为什么杀了三叔?凶手不是我跟二叔,也不是兰姨,她当时正在隔间烧火做饭,我跟二叔都看到她坐在火炕前的影子了,也不可能是奶奶,奶奶一把年纪就连下床都是问题,更何况那是她的儿子。唯一的可能就是刚刚那个女人,也就是三婶。
或者说,是四婶的鬼魂。
我们把三叔的尸体跟他被割下来的肉一块掩埋了,血淋淋的场景被黑夜覆盖,我们不敢声张,只能悄悄处理。
我跟二叔扛着锄头转到屋后,就着寒风哼哧哼哧地挖着坑,“二叔,其实我知道四婶跟三婶还有兰姨是从哪来的。”
二叔停下手上的动作,冷冷地看了我一眼,“哪儿来的?”
“买来的。”我盯着二叔一字一句地说道,“现在到处都是女大学生失联的报道,在我刚出去上学的那一年,我就知道兰姨跟四婶的身份了。”
二叔哼了一声,点了根烟,“那又怎样,她们是我们买来的,不偷不抢,我们怕啥?”
“二叔,你们这是非法交易,是要判刑的。”我瞥了眼三叔的尸体,冷笑道,“不偷不抢你们为什么不敢报警?为什么不敢给三叔出殡送葬?还不是怕事情败露!”
“败露?哼,你看看这山里有几家的媳妇不是买来的?二狗子的媳妇被他做成了人彘,三娃子的媳妇被他活活虐死。买媳妇这是公开的秘密,我们怕啥!穷乡僻壤的天王老子也管不着!”
“可是二叔,你们就不怕天谴吗?”其实相比天谴,我更害怕叔叔跟父亲,他们已经无可救药,丧心病狂,我怕他不会放过我,我有些后悔,不该捅破这一层窗户纸,可是我好奇,我想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。
“长这么大我还没见过遭天谴的呢,要遭天谴也是二狗子他们先上。”二叔吐了口痰,使劲地挥着锄头。
“那三叔呢?”
二叔停下手上的动作,忽然喊了声“不好”便往屋里跑,我想二叔跟我想到一块去了。
我尾随二叔跑回屋里,见兰姨正端着缸子喂奶奶喝水,颤抖的双手将水撒了出来,看样子她也吓得不轻。而三婶被拴在炕角上,还是疯疯癫癫的模样。
“嘿嘿嘿,她回来了,我看到她了。”三婶爬到炕沿,一脸神秘的模样。
二叔拽着她的头发将她扯到跟前,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,“是不是你杀了老三!”
三婶被打得呼天喊地,连连哀嚎。
“二叔,不是她,三叔被刮得骨肉分离,那么短的时间一般人做不到。况且,她分明是个傻子。”我不忍心看三婶被打,急忙替她解释。
“不是她,她一直跟我躺在这炕上。”奶奶悠悠转醒,声音有些沙哑,浑浊的双眼望向窗外,“是报应,报应。”
我跟二叔在一块,我俩又能给兰姨作证,奶奶与三婶一直待在一起,那究竟是谁杀了三叔,难不成真是她!
想到这儿,我拉着二叔往院里跑去,果真,槐树上出现了那个字,“咒”,血淋淋的“咒”字在月光下格外的诡异。我的腿有些浮软,脑海中是四婶死时的样子,幽怨绝望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
“操,我还就不信这个邪。”二叔拿砍刀将槐树上的字清理干净,又把三叔的尸体埋了。
一切恢复如初,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,我依旧去灵堂给父亲守灵,二叔去陪着奶奶。虽然父亲做的事令人发指,但他依旧是我的父亲。我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,感受着沁骨的寒风。
“方子,你二叔怕你害怕,让我来陪陪你。”兰姨给父亲上了炷香后就跪在我身边。
“你导师……他还好吧?”
“导师他老人家很好,虽然头发都白了,但精神矍铄,身体很好,就是师母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,不过师哥很孝顺,每天都回去陪他们。”
“师哥?”兰姨紧了紧衣领,有些惊慌地望着我。
“对,就是导师的儿子啊。喏,这是他们的照片。”
我从钱包里拿出导师一家的照片,阳光下的老头和老太太满头白发闪闪发光,中间的男生阳光活泼,笑得肆无忌惮。兰姨望着照片身子不停地颤抖,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,打湿她手上的照片。
“兰姨,二十年前您教我知识,十年前您又引导我考上那所大学,让我接近我的导师,是为了今天吗?”我望着她悲痛欲绝的模样有些想笑,“你跟他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”
“所以你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存在。”兰姨擦了擦眼泪,转过头来望着我,“方子,你真的长大了。”
“兰姨,我只想让您做我的兰姨。”我笑着望着她。
兰姨擦了擦眼泪,站起身往外走,刚走了两步又停下转过身来说道:“对了,你三叔不是我杀的,那个咒字也不是我写的。”
我的头轰的一声,凶手不是兰姨那是谁?
二十多年前,是她跟我说四婶活得生不如死,还不如一头撞死,所以我偷偷下地窖帮四婶结束了痛苦。是她说不能让父亲知道是我干的,所以教我写“咒”字,将四婶的死鬼神化。我以为三叔的死,也是她搞的鬼,不对,是她在骗我,是她想报复我,三叔一定是她杀的,可是……烧火的黑影又是谁。
白色的蜡烛明明灭灭,山雾袭来,在昏暗的烛光下蔓延,我望着父亲的尸体,手心里全是冷汗。
忽然,一阵风吹来,盖着父亲的白布被吹起一角,露出父亲青紫的脸,十年了,父亲依旧那么苍老,枯黄的糙皮皱皱地贴在脸上。明明是那么慈祥的老人,为何干出那么丧心病狂的事?我盯着他的脸,心里有些自嘲,我何尝不是丧心病狂!
待我从思绪中回过神来,却发现有个黑影映在盖尸布上,影子中的手脚以诡异的角度向上折起,与地窖中的四婶一样,我确定,那就是她!我僵硬地转过头去,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无限放大的脸,她的额头上有个黑洞,血液从中汩汩而出,我知道,我这是见鬼了。
待我醒来时,天已经微微放亮,我被绑在石磨上,冷冷地望着眼前的一幕——
二叔已经被吊死在槐树上了,奶奶满眼泪花地望着他的尸体,没有哭喊,我想她已经痛得说不出话了。
“难过吗?”兰姨走到奶奶跟前,笑着说,“我父母失去我的时候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,今天我也让你尝尝失去孩子的痛苦。”
“三十年了,我活得人不人鬼不鬼,我住在猪圈,套着铁链,被你们毒哑,被你四个儿子轮奸,被你用鞭子打,被他们用火钳烫,被打残。要不是田儿会医术,我怕我这辈子都无法说出我的遭遇。”兰姨疯了似的喊着,哭着,笑着,揪着奶奶的破袄,狞笑着,“便宜了你的老二,就这么给吊死了,不过你还不知道你大儿子怎么死的吧。”
兰姨走到我面前,似笑非笑地问我:“方儿,要不你自己说说?”
其实我知道父亲真正的死因。
“对,是我杀的。”(原题:《孽缘》,作者:绿风蓝海。来自:每天读点故事APP <公号: dudiangushi>,看更多精彩)